全国服务热线
欢迎到rng电子竞技俱乐部官网。 官方网站 !
作者认为,萌蘖出十九、二十世纪现代社会形态的,是发源于十八世纪的“双元革命”: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。提到工业革命,人们就会自然联想到飞梭、纺纱机、蒸汽机等,但实际上,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“极为平常,其技术方面的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”,在自然科学方面“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”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快速地发展靠的主要不是机器设备,而是1689年“光荣革命”后形成的现代社会体制:政治上,国王权力受商人、新贵族的限制,由议会决定国家政策;经济上,圈地运动使得土地集中,同时将小农转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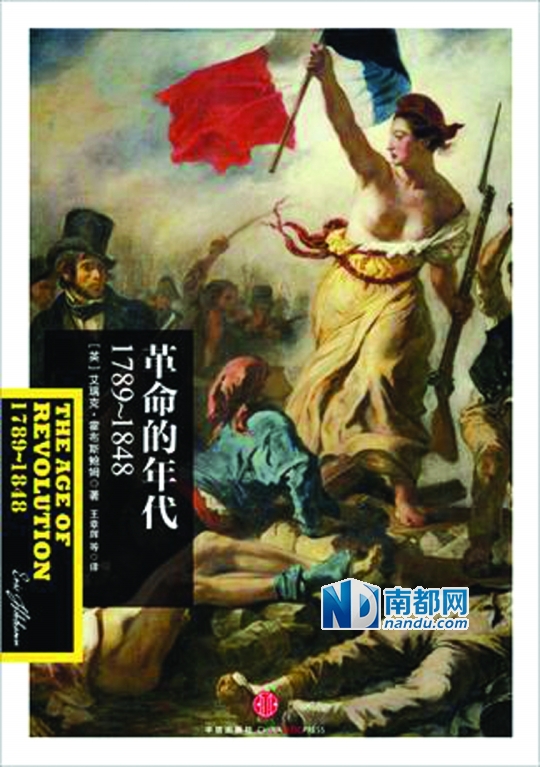
《革 命 的 年 代 :1 7 8 9~1848》,(英)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著,王章辉译,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版,48 .00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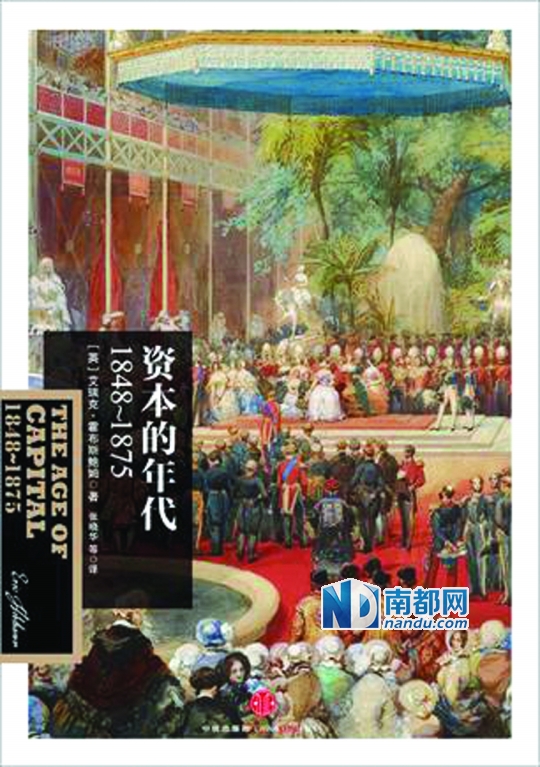
《资 本 的 年 代 :1 8 4 8~1875》,(英)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著,张晓华译,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版,48 .00元。

《帝 国 的 年 代 :1 8 7 5~1914》,(英)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著,贾士蘅译,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版,48 .00元。
在追溯战争起源时,最常见的解释,就是视其为少数君主、政治家、好战集团为满足私欲或阶级利益,驱使无辜民众相互杀戮的结果。领导层是邪恶、渴望血腥的,而充当炮灰的民众则是善良、热爱和平的———但这种传统模式,却无法解释一百年前的那场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从大量回忆录和档案资料中,历史学家们发现,1914年以前,实际上没有一个强国政府想打一场全面战争。相反,多次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表明,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才是普遍共识。一战的吊诡之处在于,所有参战国都认为,自己是被迫还手的,是在捍卫世界和平,是“以战止战”。无论德奥意三国同盟还是英法俄三国协约,其缔约初衷都是共同防御。甚至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,7月遭王储被刺之辱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,各国的第一反应都不是欣喜有了开战口实,而是尽力试图补救,对于形势的失控,各国决策层如霍布斯鲍姆所描述的那样:“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,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。”
与此相反,民间则是一片亢奋,尤其是荷尔蒙旺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,他们渴盼战争的到来,如坠入情网般“心甘情愿地、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。”听到枪炮声,他们的反应是:“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。”以和平、富足和进步为代表的欧洲十九世纪实在太过漫长了,它所带来的安定和理性已经让欧洲中产阶级发腻,浑身不自在。当下他们所渴望的,是狂暴、本能和,因为只有这些能激发活力,“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,使生命添加滋味。”
“回家过圣诞!”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,德军士兵大踏步走向战场,却在马恩(M arne)河遭到英法联军的当头一棒,六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。“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”,最大的屠宰场就是英法与德国拉锯的“西线年的“绞肉机”凡尔登战役,双方伤亡100多万;接下来的索姆(Som m e)河战役,跃升至110多万。曾经为世界贡献了工业革命、自由大、人权宣言、人道主义、启蒙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欧洲文明国家,最后竟各派几百万青壮年,日夜在壕沟里,在沙袋后,在炮弹的呼啸声中,像老鼠一般相互撕杀。
卡尔(E. H . Carr)曾言,历史是“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”,霍氏这套针对普通读者的巨著,就是在苏联解体、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际,试图重新审视十九世纪留给今人的遗产,重构现在与过去的有机联系,“记住已经被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。”
作者认为,萌蘖出十九、二十世纪现代社会形态的,是发源于十八世纪的“双元革命”: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。提到工业革命,人们就会自然联想到飞梭、纺纱机、蒸汽机等,但实际上,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“极为平常,其技术方面的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”,在自然科学方面“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”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快速地发展靠的主要不是机器设备,而是1689年“光荣革命”后形成的现代社会体制:政治上,国王权力受商人、新贵族的限制,由议会决定国家政策;经济上,圈地运动使得土地集中,同时将小农转化为城市自由劳动力;市场、利润、效率观念也深入人心。正是这些非器物层面的改变,让英国率先突破了前近代时期周期性自然灾害、政府更迭造成的社会动荡、死亡加之于生产的最高限制。
与先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曲高和寡不同,1789年法国大革命则是世界性的,“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,而且其后果要深远得多”,它完全重塑了人类对于“革命”、“民族”、“国家”的定义:“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,而且比任何一次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。”如果说近代国家的社会经济主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,那其政治理论、意识形态则是受法国革命的影响,为何会如此?
法式启蒙,与谨小慎微的英式启蒙相比,更加激动人心,且显得有“放诸四海而皆准”的普世性。罗素(B.R ussell)曾说:“在先进的国家,实践产生理论;而在落后的国家,理论指导实践。”从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到印度民族起义,从苏俄到红色中国,多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响:先由知识分子鼓吹,奠定革命共识,接着底层民众绕过中产阶级改良派和议会斗争,直接进行社会革命。
霍布斯鲍姆认为,巨大的内外压力下,革命后期法国已形成了“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”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。同时,危机过程中“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:通过征兵、实行定量配给制、严控战时经济,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,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。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含义,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晰起来。”
1806年10月,法军痛击普鲁士军,连下柏林、耶拿。当时正在耶拿大学任教的黑格尔目睹身骑白马的拿破仑皇帝入城,认为他就是“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”。1815年滑铁卢的惨败,并不妨碍“世界精神”随着拿破仑的远征军传出国界,此后所有欧洲国家的制度“没有一个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。”最典型的恰恰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最积极的德国人,他们知耻后勇,模仿法国民族国家体制并更进一步,将国家视为———按黑格尔在《法哲学原理》的著名表述———“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”,只有国家才是自在自为的终极目的,“个别的人只是些环节罢了”。
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,北德联邦军击溃法军,还俘虏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,即当年攻陷柏林的拿破仑·波拿巴的侄子拿破仑三世,一洗半世纪前的耻辱。次年,威廉一世顺势宣布德国统一。德国的崛起,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。欧洲的主要矛盾,也从英法矛盾转变为英法与德国矛盾。
在帝国主义时代,战败除了传统的割地赔款外,还意味着失去海外殖民地———胜利者赢得一切,失败者一无所有,这种局面逼迫一战与二战期间,所有民族国家都不计后果、不惜代价地投入战争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正是二战后西方的衰落,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,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,才最终给欧洲带来了和平。
进入二十世纪这个“极端的年代”后,双元革命的自我毁灭性渐渐显现。英国革命的物质成就使杀人机器越来越高效,战争“非人化”了,“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”。法国革命除了催生更多民族国家外,其高倡的人民主权也让战争“民主化”了:1789年以前的欧洲,战争多少保留着几分贵族和骑士精神,不以杀伤对手为目标,更不戮及平民,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。可是在民主化战争中,“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,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目标。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,跟民主政治一样,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,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。”在这种基础上的总体战,只会不断突破底线。
霍布斯鲍姆认为,战争越来越残酷,后者的因素还更大一些。自由民主政体的弊端,至少在那些已实现它的国家中,恐怕还尚未被充分认识到。民众永远是短视的,人口和生态危机、福利国家的难以为继、民族主义的相互激荡,都显示了这一点,福山式的“历史终结论”根本站不住脚。霍布斯鲍姆没有给四部曲留一个光明的结尾,而是尖锐地警告道,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十九世纪二元革命产生的旧基础上建立新千年,那是注定要失败的,“失败的代价,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,将会是一片黑暗。”